对于同一个人,如果一些人毁之为乱世奸雄,而另一些人却誉之为救世英雄,那么,世人就陷于“毁誉迷雾”而无所适从了。这种迷雾,也会出现在对社会、民族、国家的评价上。对此迷雾,是否有适当解释呢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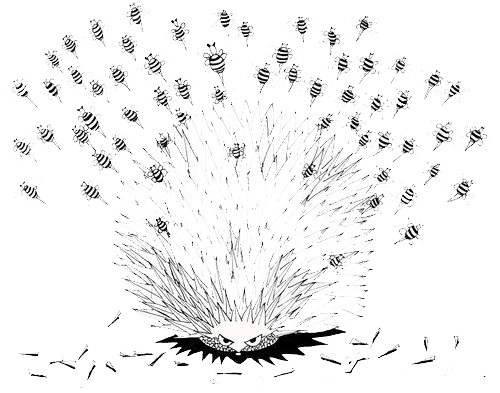
### 毁誉之间
对于前苏联,誉之者曰“人间天堂”,毁之者曰“人间地狱”。一个毫无成见的人,面对如此恰恰相反的评价,想必会如堕五里雾中,莫衷一是。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,人们因此而陷入迷雾,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。
评价一个国家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,因此几乎不可能有唯一公认的结论,它依赖于观察者的价值观、视角、客观性与偏好等多方面的因素。仅仅价值观的不同,就会使各执一词的人完全无法沟通。就是不考虑价值观,而仅限于考虑观察方法与评价态度,也可能出现两种极端的评价:
**客观评价** 指由全面的证据支撑的公正评价,它兼有观察的全面性与评价的公正性。全面性可以基于观察者被公认的科学声誉,亦可以基于许多人观察的综合。公正性意味着不带偏见,这个要求比看起来要复杂,实际上很难界定。什么叫偏见呢?或许解释偏见的人就有偏见。况且,严格说来,你到哪里去找毫无偏见之人呢?
**主观评价** 指完全依据个人好恶的评价,它仅仅反映了评价者的喜好,不具有任何科学价值。
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是互相对立的:客观评价解决好坏问题,是一种价值判断,它是需要论证的,具有一定的稳定性,不会因个别观察者看法的改变而随意变化。主观评价表达爱憎,可能表面上也有价值判断的成分,但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倾向表达而已;它不需要也不可能论证;因随意性太大而完全不稳定。
还有一种相关但不同的评价,它就是“重要性评估”,它解决影响力的大小或者轻重问题,具有一定的客观性。原则上,轻重之不同于好坏、爱憎,是毫无疑义的;但现实生活中常常混淆不清,造成逻辑混乱。例如,如果你说“纳粹德国是一个重要国家”,或许立即就会有人驳斥你:重要个屁!最坏的国家,我最恨它。这就在逻辑上不通了;重要、最坏、可恨三者是不同的概念,既不矛盾,也不重叠。
至此已可谈“毁誉”。“誉”兼有肯定的价值判断与喜爱表达;“毁”则兼有否定的价值判断与憎恶表达。因此,“毁誉”兼有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的特质,既有一定的客观性与稳定性,亦有一定的主观性与随意性。毁誉的客观性不及客观评价,完全可能与事实有很大差距;而其主观性则不及主观评价,故并非纯粹的个人偏见,其影响不可低估。“毁誉”的份量,与其客观性成正比,而与其主观性成反比。客观性无疑强烈地依赖于毁誉者的公正性。
毁誉势同水火,竟同时加于一国,不免显得矛盾,呈现出某种奇观;但实际上频现于现实中,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。当然只有重要的国家,人们对其毁誉才感兴趣。例如,谁会去关心对老挝的毁誉?另一方面,也只有来自重要观察者的毁誉,才会有人感兴趣。例如,泰国海滩上某个无知渔民,对中国无论是誉还是毁,大概都成不了新闻。因此,引证名人的毁誉之见,并不算偏颇。
现在先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解释以上分析。
不妨考虑战后的日本。有许多学者关注战后日本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国际关系等等方面的表现,或许能够给予某种“誉”。至于“毁”就各式各样了,例如认为日本就是一头经济动物,唯图利益而不顾道义,至今不肯承担二战的责任。无论誉与毁都有一定的客观性,尤其对于中立的研究者,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进一步的事例包括古代中国、前苏联、今日美国。
### 古代中国
现代中国人最想听到西方人的赞誉,也最不能承受西方人的刻意毁损。至于古代中国,则根本就没有这种缘分,那时东西方完全隔绝互不与闻。但大约从中世纪末开始,有关中国的信息就通过传教士传入西方,在西方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。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士,对于遥远的东方大国充满了兴趣,出现了评议中国的某种热潮,当然毁誉兼有,程度也各有不同。
莱布尼兹(1646—1716)是与牛顿齐名的德国学者,是当时欧洲最推崇中国文化的人士之一。他甚至声称,“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,就是大陆两端的二国:欧洲及远东海岸的中国”。在中国的太极学说中,他发现了他发明的二进制的原型。
伟大的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(1694—1778),是中华文化的另一个主要崇拜者。他认为“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”,中国人是“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”。他完全肯定中国的制度:“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,即使不至五体投地,至少可以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最好的,而且是唯一建立于父权宗法之上的”;“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组织”。
英国思想家休谟(1711—1776)认为:“中国是世界工业最繁荣的帝国的代表之一”。高估古代中国经济成就的西方学者,不在少数。
不同于上述的誉甚至是过誉,另一些看法则显得负面。
《鲁滨逊漂流记》的作者笛福(1660—1731)借鲁滨逊之口说:“中国人的器用、生活方式、政府、宗教、财富和所谓光荣,都不足挂齿”;“他们对于天体运行一无所知,愚蠢无知之极,以为日蚀是大龙抱了太阳”。这已经是毫无顾忌的毁损了。
意大利思想家维柯(1668—1744)的评价严峻而别开生面:“中国人和古代埃及人一样,都用象形文字书写……正如一个人在一间小黑屋里睡觉,在对黑暗的恐惧中觉醒过来,才知道这间小屋比手能摸到的地方要大得多”;“孔子的哲学,像埃及人的司祭书一样,在少数涉及物理自然时都很粗糙,几乎全是凡俗伦理,即由法律规定人民应遵行的伦理”。
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(1689—1755)主要关注法律制度:“(评价大逆罪)因为没有规定什么叫不敬,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”;“如果大逆罪含义不明,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”;“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并行,但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,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。中国的专制主义,在祸害无穷的压力之下,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戴上锁链,但却徒劳无益;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,而变得更为凶残”;“中国人的生活以礼为指南,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。”;“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,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力和异乎寻常的贪欲,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”;“在表面上似乎最无紧要的东西,却可能和中国的基本政制有关系。这个帝国的构成,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”。这些鞭挞,已深入骨髓了。
大哲学家黑格尔(1770—1831)如此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:“光荣在于‘唯一的个人’,一切皆隶属于它,以致任何其他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”,他的“唯一的个人”指君权。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幼年文化,“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”,臣民都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。
上述学者都没有到过中国,接受中国信息的渠道也未必太多。之所以评价相差悬殊,自然与各人视角及立足点的不同有关。
### 前苏联
如果一个大帝国——而且是刚刚靠掠人之地而扩张了的大帝国——在全世界广受赞誉,那就是前苏联了。我就是在对苏联的一片颂歌中长大的,对苏联如何被描绘为天堂,至今都印象深刻。
苏联的最大成功或许在于,它在敌对阵营中赢得了大批支持者,而且是很有身份的支持者——一些地位崇高的西方知识分子:学者、作家、艺术家、记者等等。
西方知识分子都有一个通病,那就是不喜欢自己的政府,而耽于幻想,喜欢听来自天边的圣歌般的声音,以为那就是真正的福音。在20世纪上半叶,他们发现的现世天堂就是苏联;他们听到的从苏联传来的一切,无不带有天堂的特征:消灭了剥削、压迫、歧视、乞丐、妓女、盗贼等等人世间的一切丑恶现象,实现了普遍平等、共同富裕、共享权力等等。对这一切深信不疑的那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,大受鼓舞,激动万分,对苏联的向往,成了他们的灵魂的安慰剂。他们生活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中,并不忌讳公开喊出“支持苏联”的口号,而这正是苏联最想听到的。
在这些知识分子中,有几个最著名者可作为代表人物,他们就是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、纪德,爱尔兰作家萧伯纳,这三人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;都应邀访问苏联并得到国王般的接待;都对苏联发表过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。罗曼·罗兰(1866—1944)是最早歌颂十月革命的法国作家,坚持认为唯有苏联才能够拯救西方,称十月革命是“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开拓性革命”。纪德(1869—1951)也是苏联的热情支持者。萧伯纳(1856—1950)在1930年代的演说和文章中,对苏联作了热情的赞颂,高度称赞“苏联人民的卓越成就”。
到西方社会去寻找对苏联的批评,当然毫无困难。但最发人深省的是,一些尖锐的批评恰恰来自苏联曾经的坚定支持者。例如,正是对苏联的访问击垮了罗曼·罗兰与纪德对苏联的崇拜。纪德经过一番犹豫之后,决然地发表了他的访苏日记《访苏归来》,其中记述了那些他无法容忍的东西:虚假、压制、特权、个人崇拜等等。随着莫斯科大镇压的愈演愈烈,纪德最终忍无可忍,于1937年与苏联正式决裂。有同样心路历程的罗曼·罗兰,却采用了稍不同于纪德的方式:在斯大林的大镇压之后,他对苏联已不再抱有希望,但还是选择了沉默,将他的访苏日记的发表推迟到死后。
上述例子中,对苏联的毁誉源于同一个人,这一点也不矛盾:苏联还是那个苏联,但观察者却在了解真相之后改变了看法。
### 美国
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已达百年之久的美国,早就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;它所承受的毁誉之多,自然非他国可比。美国树大招风,对之加誉加毁,都是很平常的事情。但如果这种毁誉来自同一出处,且当事者从不觉得此中有什么别扭,那就真是天下趣闻了。世界上毁人者与誉人者都有无数,但如上述奇事想必不多。因此,如下史料才倍显珍贵,不妨录下共享:
** 每年这一天,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;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,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。167年,每天每夜,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——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,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。**
**从年幼的时候起,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。我们相信,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,她也没有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;更基本地说,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,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,博大的心怀。(《新华日报》1943年7月4日)**
对于一个友邦所用词汇之友好且动情,实在莫过于此了。你能不相信这些表达都是很真挚的吗?这些文字能够感动每个读到它的中国人。
但是,正是写下这些文字的人,没有多久之后,就写出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番话语:
**美国到处欠账。欠中南美国家、亚非国家的账,还欠欧洲、大洋洲国家的账。全世界,包括英国在内,都不喜欢美国。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。日本不喜欢美国,因为美国压迫日本。东方各国,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。它侵略中国的台湾省。日本、朝鲜、菲律宾、越南、巴基斯坦,都受到美国的侵略,其中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。人民不高兴,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。(《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》,1956年7月14日)**
此处岂止不再有对美国的好感,实际上已视美国为仇敌了。不清楚的只是:是美国堕落得太快,还是毁誉者变化得太快呢? hiveblocks
hiveblocks